
新闻链接:《生命时报》 第1909期 22版
发布时间:2025-7-4
作者:路桂军
经常听到临终患者对我说:“我放下了。”其实,他们所说的“放下”,并不等于看淡生死,而是开始直面生死。“放下”这个词的出处可能来源于佛学,通常 指的是舍弃执著、放下贪嗔痴,达到无我境界。而临终患者的“放下”,实际上是积极地面对,而非消极地逃避。
传说,佛陀在菩提树下顿悟的刹那, 洞见“放下”的本质绝非消极的舍弃,而是一种新生。佛教经典《杂阿含经》里记载,当弟子询问如何面对死亡时,佛陀拈起一朵曼陀罗花说:“观诸行无常,是生灭法。”这个著名公案揭示,佛教的“放下”是穿透生灭表象的智慧凝视,要求修行者将生死置于台上,如同待鉴的珍宝般郑重陈设。因此,佛学的放下是建立在对生命的全然担荷之上的。
而临终者说的“放下”,实质则是“放上”。前不久安宁疗护病房入住了一位肺癌晚期的李先生,他说自己烧掉了一生荣获的所有奖状,对我们说:“我放下了。”我看到当时他的眼神并非空洞,而是穿透生死的澄明。李先生的这一“放下”,实则是从逃避到直面,是将生命本质从世俗的潜意识中抽离,置于理性与情感交织的“桌面”上,这是对他自身存在的重新锚定。
王女士的母亲乳腺癌晚期全身多发骨转移。清晨上班路上她接到妈妈的电话,“我上厕所不小心摔倒,全身四处多发骨折。”找到我的时候,王女士全程自责:“妈妈都到这个时候了,我还上的什么班?为什么我没在身边?妈妈原本就没有多长时间了……我无法原谅自己。”
我问她:“妈妈怎么说?”“妈妈说都是她不小心,又给我添麻烦。可妈妈越是这么说,我越自责,我无法接受妈妈仅剩的时间里还在痛苦中度过……”我跟她说,在有限时光里,放下纠结坦诚对话,用温暖替代遗憾,当离别时刻真正来临,与亲人共同正视死亡,并非是对亲情和生命的背叛,而是一种勇敢与尊重。
因此,在临终关怀病房的静谧中,患者口中的“放下”不能理解为对生命的消极弃绝,而恰恰是对无常法则的认同与超越。现代医学有时将这种状态归因于心理防御机制,却忽视了其哲学维度。 庄子提出的“生死齐一”论,揭示了“放下”与“放上”的辩证统一:当患者停止与死亡对抗时,实则是将生命的整体性重新确立。
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基于401份死亡叙事的研究发现,中国临终者的自主决策率不足20%,多数选择被家庭伦理裹挟。我曾经见过一个白领女性,父亲弥留之际,要求我们输入高级别营养液。她的理由是:“我爸爸现在不能吃饭,这就是他的口粮;我怎么可能让我爸爸饿着,我要给他输最好的营养液。”但此刻的患者已经多脏器衰竭,处在离世的边缘,这些“爱心营养液”只会加重病重父亲的心肺负担,让他更加痛苦。女儿的这种对死亡的抗拒,折射出整个社会对生命规律认知的集体焦虑。
对生命规律认知的集体焦虑。 生死幕布后的真实,是医学与哲学的共生,而“放下”才是生命觉醒的起点。在终极意义上,每个临终者的“放下”,都在为人类集体意识书写最庄严的生命认知宣言。
上海某安宁病房里,医护人员引导患者制作“生命锦囊”,将未竟之事转化为象征物纳入锦囊。这个仪式化的“放上”过程,使93%的患者报告获得了存在意义感。某个胰腺癌患者将未能出版的书稿化为纸鹤放入锦囊后,在临终日志中写道:“我终于把死亡变成了生命的出版社。”
总之,放下不是终点,而是将生命重量郑重托付给存在本身。正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,唯有松开执念的缰绳,方能乘风起舞。所以,执业安宁者要尊重每一个“放下”。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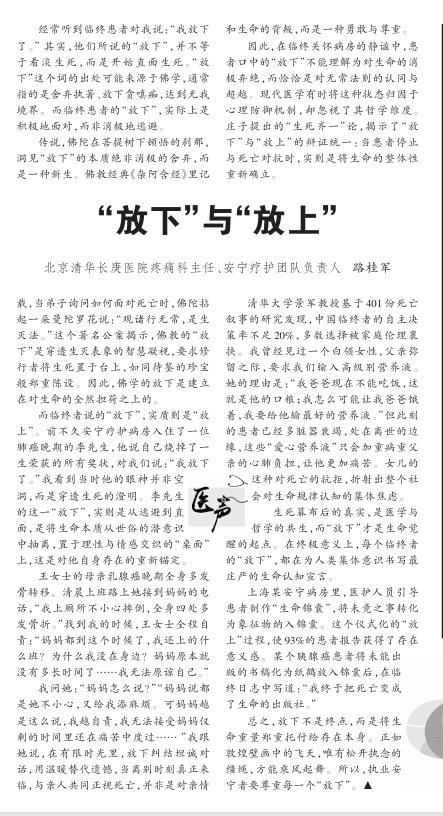

北京清华长庚医院APP
快速挂号